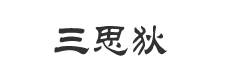犬儒主义(cynicism),亦译“昔尼克主义”。西方古代哲学、伦理学学说。主张以追求普遍的善为人生之目的,为此必须抛弃一切物质享受和感官快乐。其所以称为“犬儒”,一是由于其创始人是在雅典一个名叫“快犬”的运动场讲学;二是由于其信徒生活艰难,在大街上讲学时衣食简陋,随遇而安,形同乞丐, 被人讥为犬。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为雅典的安提斯泰尼。
名字起源
“犬儒学派”这个名字的由来有两种解释,或说该学派创始人安提西尼曾经在一个称为“快犬”(Cynosarges)的竞技场演讲,或说该学派的人生活简朴,像狗一样地存在,被当时其他学派的人称为“犬”。
到现代,“犬儒主义”这一词在西方则带有贬义,意指对人类真诚的不信任,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的态度和行为。
现代犬儒主义
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现代犬儒主义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犬儒主义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
“说一套做一套”形成了当今犬儒文化的基本特点。“世界既是一场大荒谬,大玩笑,我亦惟有以荒谬和玩笑对待之。”
犬儒思想并不带有自我罪孽感。在它那里,怀疑正统成为一种常态思想。无论从认知还是从道义来说,不相信都是常态,相信才是病态;相信是因为头脑简单,特容易上当。犬儒思想者也不再受恐惧感的折磨,因为他知道人人都和他一样不相信,只是大家在公开场合不表明自己的不相信罢了。
它是一种对现实的不反抗的理解和不认同的接受,也就是人们平时常说的“难得糊涂”。犬儒主义者意指并不真傻的情况下,深思熟虑地装傻。既然我没法说真话,那么你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不这么说也得这么说,由不得我心里想说什么。我照你的说,不见得有好处,但不照你的说,说不定就有麻烦。我知道我照你的说,你未必就相信我,未必就拿我当回事;但我不照你的说,你肯定会说我不拿你当回事。既然你要的不过是我摆出相信的样子,我又何必在说真话上面空费心思。
当我们谈论犬儒主义,我们在谈论什么?

古希腊哲学家、犬儒学派的创始人第欧根尼,住在借来的大桶里,放弃一切对物质的享受与舒适的追求。(视觉中国/图)
“我希望你闪到一边去,不要遮住我的阳光。”古希腊哲人第欧根尼对来访的亚历山大大帝说。
这是关于古代犬儒主义流传最广的传说。据说第欧根尼住在一个木桶里,所拥有的财产仅仅只有这个木桶、一件斗篷、一根棍子和一个面包袋。有一次第欧根尼正在晒太阳,亚历山大大帝前来拜访,问他需要什么,并保证会兑现他的愿望。于是第欧根尼对大帝说出了这句庄子式的妙语——就像庄子对楚威王的使者说:“子亟去,无污我。”
来自锡诺普的第欧根尼是古希腊最知名的犬儒主义者,他及其追随者们的生活方式与当时社会的文明教化格格不入,甚至行事不顾礼义廉耻——他们用放屁来代替寒暄,为此他们不得不吃很多豆子,以保证有屁可放;最极端者还会当街排泄——这群人被加上了 “像狗一样”(英译为doglike)的称呼。这就是“犬儒”之名的由来。
和我们现代人一样,古希腊人对“狗”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犬儒的“狗样” 所强调的,绝没有“卑躬屈膝”和“摇尾乞怜”的意思,而是这群人和狗一样全然服从自然冲动的支配,不顾习俗所要求的基本行为礼仪,在大街上“如狗一般地”处于 “野生”状态。“古代犬儒主义以对抗性、挑衅性的举止来宣扬自己的存在。古代犬儒们所要做的,就是揭示希腊式教育乃是一个诡计,是一套任意专断的文化价值,是贵族们的伪饰,以抬高他们的身份。”英国学者安斯加尔·艾伦在他的书《犬儒主义》中说道。
《犬儒主义》是一本关于这个概念的流变史的通俗著作,安斯加尔·艾伦在书中不仅梳理了“犬儒主义”概念内涵的古今之变,也揭示了隐藏在这个概念背后的社会心理的复杂性,“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还原犬儒主义的所谓真面目,而在于激活犬儒主义这一源远流长但始终晦暗不明的思想潜流的‘真精神’。”本书译者、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倪剑青说。
安斯加尔·艾伦将犬儒主义分为古代犬儒主义和现代犬儒主义,这也许是理解这个概念在现代生活中依然有理论活力的关键一点。
以第欧根尼为代表的古代犬儒们,通过攻击作为病因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惯例来实现改变“人之恶习”。用福柯的话说,这种恶习“形成于、依赖于、植根于人们的习俗、行事方式、法律、政治制度与社会惯例之中”。古代犬儒们用自己的行为进行一场“明确的、故意的、持续的侵犯”,设法引起公众的愤怒,从而使那些不加思考的承诺浮出水面,变得可见,并使得矫正成为可能。
古代犬儒的真实目的是“通过揭露文明的矫饰伪装,在祛除了‘人为的’扭曲之后,让人之真正的德性得以显露,并保持‘自然的’纯洁。毫无疑问,权力、制度、体制,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权势、财富等等,这些东西对于犬儒派而言,是需要尽早拋却殆尽的污垢。”艾伦在书中写道。
然而,当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在谈论犬儒主义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呢?当我们指着某人说,这个人是个犬儒主义者,这里所包含的意思,似乎与古代犬儒派的想法并不一致。很显然,犬儒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古典哲学术语,也是一个当代生活中我们会经常使用的常用词。对于现代大多数人来说,犬儒主义的真正意涵变得有些模糊不清,甚至这个词本身,从古至今也经历了不小的意义转变。这才是安斯加尔·艾伦通过《犬儒主义》所要重点讨论的话题。
“现代犬儒主义是西方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艾伦讲述了现代犬儒与古代犬儒之间的区别。在经历了上千年的演变之后,现代犬儒和古代犬儒尽管都对他们身处其中的体制感到失望,但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夸张的失望状态。他们对政府治理的不足之处、体制的腐败的反应模式,近乎巨婴”。艾伦说,“当没有收到他们心目中恰当的回馈时,这些当代犬儒就主动地切断了与真实世界的联系,将他们的失望转化为一种武断的判断:所有机构与体制都有着不可避免的缺陷,因此只能对它们报以漠视。这些当代犬儒觉得,他们什么都做不了,所有努力终将白费。因此他们抛弃了个人责任,决心对政治保持冷漠。他们哀叹一切已然败坏。但就在他们的放任之中,对美好之物的侵蚀却进一步加剧了。他们亲手促成了它。”
很多西方当代观察家和媒体都对这种现代犬儒主义的危害有详细的评述,他们认为现代犬儒主义的蔓延至少要为以下这些社会顽疾负责:“从政治冷漠、文化衰退、对启蒙理想失去信念,到自由民主制度的内部衰退。”艾伦说,“当代社会中,西方民众对自由民主政体的体制性价值和文化性价值普遍缺乏认同,从而缺乏投入的热情与行动。它还引发了对真理、专业知识以及权威的全面且无限制的怀疑与猜忌。现代犬儒主义的特点就是怀疑与退缩,他们对高尚的理想报以怀疑,从公共领域退回到私人生活的领域,而在私人生活中他们又充满了怨恨。集体冷漠成为了西方民众持有现代犬儒主义的必然结果。”
艾伦还将观察的视角转向他所在的学院内部,提出了“学院派知识分子的策略性犬儒主义”的概念。他注意到,在知识分子内部,现代犬儒主义正在蔓延,“对于我所了解的大学系统的雇员来说,某种程度的策略性犬儒主义是无法避免的。只是有些人在这个系统中工作得更如鱼得水,比其他人更没有顾忌。”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尽管现代犬儒主义被诸多学者描述为一种社会痼疾,但艾伦并不打算全盘否定它。对他来说,现代犬儒主义内部隐藏着一种“造反的潜能”,和古代犬儒主义一样,它显示了“一种不同的生活”的可能性。实现这种可能性的前提,是要使目前的尘世秩序完全地崩溃——即“从毁灭那种导致剥削、污染和生态崩溃的全球经济秩序,到彻底调整那些占有我们并存在于我们之中的主观性”。现代犬儒们并不期待某种“革命的奇点”,而是通过他们的冷漠“使(现行体制)变得更不可理喻,同时也使之不断地具有变革的特质。他们不需要模仿古代犬儒派的挑衅性和对抗性的行为,这并不是说挑衅和对抗已经从现代犬儒的武器库中被排除了”。
对于艾伦的这种略显天真又激进的观点,本书的译者倪剑青并不认同。“在我看来,艾伦博士过分乐观,试图在现代犬儒主义之中寻找积极的革命性因素,试图通过广泛团结来使得现代犬儒主义成为某种人类解放的助力——哪怕是一种消极的内心抵抗力。”倪剑青说,“但很不幸,西方世界之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犬儒主义并不会拥有撕开铁屋子的能力。”
“铁屋子的自我崩溃的确与犬儒主义的腐蚀作用有一定关系,那是因为权力者自身也被腐蚀,从而动摇了自我保卫的意志与决心。但让铁屋子崩溃的那一击,从来就不是无法协同行动的犬儒派能完成的,不论是古代犬儒,还是现代犬儒。而且在崩溃之后,如何才能真正实现解放,而非陷入更大的虚无泥潭,以致建造起一间更大更牢固的铁屋子,这一无比艰巨的任务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这更不是犬儒主义能承担的历史重任。我们今天去了解犬儒主义,除了兴趣之外,关键在于提供一个契机,去思考如何定位我们自己。”倪剑青在本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从古典时代到“一个漂浮的符号”
南方周末:为什么后世的人都会将古希腊时期的犬儒主义者理想化?你在书中是否也某种程度上理想化了古代犬儒主义?
艾伦:人们对古代犬儒主义的了解仅仅来自于一些轶事,这些轶事记载了著名的犬儒主义者说过或做过什么,如第欧根尼、安提斯泰尼或克拉特斯。当后世将犬儒主义理想化时,那些与犬儒主义的勇气或聪明才智相关的轶事被挑选出来,并得到了强调。而当犬儒主义被当作典范或值得效仿的生活方式时,这些复述他们的故事往往会淡化或稀释犬儒主义者更令人恼火和丑陋的行为。
在《犬儒主义》一书中,我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这种解读。我试图回到它所处的历史语境的逻辑,探索一个狡猾的、即兴的、不雅的和低级的犬儒主义,而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即便当犬儒主义者做了一些丑事,这种丑事也是为了证明他们对更高理想的承诺。
比如,当锡诺普的第欧根尼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地顺从自然的召唤(即当众排泄)时,这可能被理想化地解释为对其天性的庆祝,作为我们不应该对我们的身体及其排泄感到羞耻的论据。在这种情况下,丑行和游戏性的行为被解释为是由一套更严肃的哲学信条所支撑起来的。但这将是我试图避免的那种理想化的解释。
但我把重点放在丑行本身,并认为犬儒主义者正在寻求质疑禁忌,以引起人们对统治我们的成文或不成文法的注意。通过无视或颠覆这些法规,犬儒主义者暗示它们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暗示,这些约束是可以被质疑的,我们可以用实际行动质疑它们,而不仅仅是智识上的。很可能我也把古代犬儒主义理想化了,但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也就是说,我把他们描绘成某种反传统者,某种对我们生活其中的理念和法律的破坏者和质疑者。
南方周末:犬儒主义在基督教的起源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基督教从犬儒主义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滋养?
艾伦:这是犬儒主义历史上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领域,尽管犬儒主义有着下流的名声,但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不断出现在一系列基督教文献中,这一点非常特别。在这里,犬儒主义者有时再次被理想化,有时又因其不道德的行为而被强烈反对。这一切都取决于犬儒主义传统中的哪些因素得到了强调,以及如何解释它们。
基督教的早期历史也很耐人寻味,因为第一批基督教教派有时被视为与所谓的街头犬儒主义相似,至少他们都拒绝财富,拥抱贫穷。隔了这么长时间来看,很难区分他们之间的区别。也有相当多的学者提出,基督本人可能是某种犬儒主义者,或者可能与犬儒主义者有过接触,受到他们的影响。我想大家的共识是,都倾向于认为基督与犬儒主义是有联系的,但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南方周末:街头犬儒派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它继承了古代犬儒主义哪些方面的特质?
艾伦:人们对罗马时代似乎存在过的街头犬儒主义知之甚少,因为我们很少得到他们的讯息,而且是从那些对他们的存在感到不满并主张必须消灭他们的评论家那里。在4世纪,罗马皇帝尤利安建议把他们“用石头砸死”,因为他抱怨街头犬儒主义对他的士兵和下层公民有恶劣影响,他形容他们“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或从一个营地到另一个营地,侮辱所有这些地方的富人和名人,同时与社会的渣滓为伍”。在此之前两个世纪,罗马作家琉善把他们称为“狗的队伍”,并声称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没有文化,他把这种低级形式的犬儒主义和当时已经与之分离的高级、高雅或文学的犬儒主义区分开来,他认为前者是一种虚假的犬儒主义。
如果这是真的,街头犬儒没有受过教育,没有文化,那么他们与古希腊的犬儒们是不同的,例如,克拉特是一个富人,他把自己的财富捐出去,而第欧根尼显然是有文化的,精通修辞的艺术。然而,第欧根尼和克拉特都生活在街头,处于贫困状态。当时还不存在高级和低级犬儒主义之间的分离。
我自己对假设这些街头犬儒们代表了一种虚假的,或更低级的犬儒主义持谨慎态度。很有可能的是,他们的激进主义延伸到如此之深的地步,以至于他们无法再被受过教育之人的文化所收编或了解。古希腊的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克拉特、安提斯泰尼等等),尽管他们如此敌视这种文化,但他们仍然是这种文化的一部分。
南方周末:为什么在启蒙运动时期,犬儒主义变得更受哲学家关注?
艾伦:在所谓的启蒙运动中,萨德、卢梭和狄德罗等人物对犬儒主义思想进行了各种利用,他们对其吸收的情况是复杂的。从广义上讲,人们可能会说,犬儒主义对于启蒙运动的吸引力在于,它塑造了一种对理性的追求,无所畏惧地追求争论,这种追求勇敢到了鲁莽的地步,以至于这样做时完全顾不上启蒙思想家所寻求的使自己从传统限制中解放出来的议题。犬儒主义者最后一次与哲学家的“合作”也与它的最终毁灭有关,或者至少与它的激进主义的最终衰竭有关,因为它被置于理性或对自主性的追求之下。只有在萨德的作品中,犬儒主义才作为一种潜在的危险、爆发性的力量而存在。
启蒙运动可能被认为是古代犬儒主义及其“被驯化”的漫长历史中的最后一个“高水位点”。在这之后,像第欧根尼这样的人物就不再突出,也不再被当作模型或典范来使用。事实上,在今天的教育中,人们有可能不经意间看到第欧根尼、克拉特等人,但这些人物和他们的各种故事已不再是公共文化的一部分。于是,现代犬儒主义在这里出现了,因为古代犬儒主义终于被遗忘了。这种现代犬儒主义不再与它悠久的轶事和理想化传统相联系,“犬儒主义”这个词也成为了一个漂浮的符号,或者至少是一个忘记了历史的名词。
“犬儒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反传统的历史”
南方周末:很多人认为现代犬儒主义对我们身处的世界是一种威胁,要怎样理解这一判断呢?你在书中为现代犬儒主义辩护,认为它存在着某种“造反的潜能”?你做出这个判断的理由是什么?
艾伦:我提出这个论点是为了回应一个几乎无处不在的假设,即现代犬儒主义是不好的,它标志着心理或社会的缺陷,需要通过某种补救措施来解决。这种现代犬儒主义被当作一种需要治疗的个人疾病来对待。现代犬儒们被认为是他们消极态度的受害者。这种消极性被认为是过分夸大的,现代犬儒也变得过度失望。当一切都还没有失去时,他们就已经反应过度,似乎已经放弃了希望,遭受着生活动力的丧失,这本身又成为一种自我映照的预言,使现代犬儒陷入一种政治冷漠的状态。现代犬儒已经判断一切都很糟糕,因此决定什么都不做,这种犬儒被认为是喜怒无常、孤僻和脾气暴躁的,通过放弃事情可以被改善或变得更好的想法,现代犬儒最终选择了简单的方法——放弃。最后,成为犬儒是一个人可以做的最没有勇气的事情。
所有这些都可能是真的,但这并不是现代犬儒主义的全部。它的失望,它的瘫痪和无望的感觉,实际上可能传达了对一个社会、一种文化的困境的残酷的诚实,成为现代犬儒可能是已经意识到事情已经出错的第一步,正是在这里,现代犬儒的消极态度可以成为某种动力,它将失望推到一个如此之深的境地,以至于只有绝对的、激进的行动才是可以被考虑的出路。
南方周末:你提出了现代犬儒主义的各种变体,它们非常不同,像刚刚提到的知识分子的策略性犬儒主义、家长制现代犬儒主义、现代进步主义教育者的犬儒主义等等,你为什么要制造这么多关于现代犬儒主义的术语?或者可以问,是什么样的共同点让它们都可以被称为犬儒主义,而不是给它们冠以不同的概念?
艾伦:是的,这些是“积极的”现代犬儒主义的三种主要形式,这意味着它们描述了通常不会被认定为犬儒的活动类型。在某种程度上,将该术语扩展为各种子类别是为了摆脱或削弱将犬儒主义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标签的做法,并为该概念的使用引入更大的精确性。我也希望通过这样做表明现代犬儒主义没有共同的标准,就像我试图避免提供一个共同的标准或一个中心理想来组织古代犬儒主义。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犬儒主义在我看来都是由各种不同的思想组成的,它们以各种不同的配置组合在一起。这使得我们很难有效地谴责,或赞美犬儒主义,因为它仍然很难被完全掌握。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提到了特朗普的上台与现代犬儒主义的关系,但很多人认为特朗普的上台与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有关,你如何理解现代犬儒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关系?
艾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词都被用来试图解释某些极其复杂的现象。因此,说特朗普的崛起与现代犬儒主义有关,或者说它与民粹主义的兴起有关,其实本身并没有真正说明什么问题。这一切都需要在细节中详细分析,但现实是人们往往并不这样做。所以民粹主义和犬儒主义一样,都成为了万金油一样的术语,用来指代那些仍然定义不清的东西。它们都作为一个否定或拒绝的术语而被使用。
关于现代犬儒主义的问题,至少有两种主要形式在发挥作用。首先是那些在社会秩序中处于相当底层的人的犬儒主义,他们对西方民主制度产生了某种怀疑;其次,是那些像特朗普这样的人的犬儒主义,他们部署了一种更强大的、操纵性的犬儒主义,利用某些机构作为统治和分裂的工具。通常情况下,当我们识别现代犬儒主义时,它往往厕身于普通民众中,而忽略了它在社会秩序的更高层次的存在,我认为这很有问题。
南方周末:很多哲学家会想要复兴古代的犬儒主义,比如像斯劳特戴克为现代犬儒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复兴古代犬儒主义,你似乎不认同这样的主张,你觉得他的方案的问题在哪里?
艾伦: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与我对古代犬儒主义的理解有关,它是一种没有普遍原则的哲学,而且总是有针对性地处于某种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时刻,并与之产生联系。对我来说,试图恢复或重做第欧根尼(或任何其他古代犬儒主义者)的行为,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最多只能尝试理解古代犬儒主义在其特定语境下是如何运作的,并从它所处的狡黠的游戏性行为中获得灵感。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