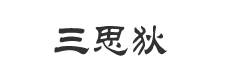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
简单地说,就是某些传统王朝的赋税改革,将前面滥征的各种摊派与附加,与正税合在一起一并征收。
黄宗羲定律下的帝国财税陷阱

明中后期开始,东北女真建州三卫的势力不断拓展,逐渐边缘化了明廷的东北卫所。终于,努尔哈赤在1616年建立八旗制并建立汗国,不久又以“七大恨”为由正式起兵反明。隔年,萨尔浒之战爆发,满洲八旗击败杨镐指挥的明、朝与叶赫联军,对北方明军精锐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满洲八旗携余威先后接攻占辽东重镇沈阳、辽阳、抚顺等城池,明帝国的辽东防线土崩瓦解,虚弱的军政体制一败涂地,帝国都城暴露在了北方铁骑之下。于是,已经酝酿许久的饷银加派开始迅速贯彻,随后并为“三饷”推行。但这一举动恰恰背离了早年间“一条鞭法”税制改革弥补的躯壳,这一举措杂糅着自上而下的混乱,使得原本就已虚弱不堪的财税体制迅速恶化,促成了明帝国的瓦解。晚明财税改制成为黄宗羲笔下的“积累莫返之害”。这一切到底有怎样的因果呢?

辽东战事吃紧,边关饷银拖欠,关内民变四起……情势已经万分火急,此时的万历朝经过三大征已经国库亏空,内帑略有盈余,但“帝靳不肯发”。无奈之下,明廷朝臣只得转向张太师的遗产——一条鞭法及折算白银。当然,此时有着历史大背景的背书。
明初,太祖曾专旨划定财税制度,发行“大明宝钞”并禁止民间用银交易。这一制度意图将整个帝国彻底扁平化,排斥掉宋元以来发达商品经济对政权的威胁。这样的制度设定下,终明一代的征税水平始终徘徊在过低状态(“三十而取一”左右),以至于难以为官僚系统的运行提供基本公共产品。但这一设定越来越难以满足帝国运行的需要,加上十六世纪中后期以来美洲白银的大量输入,原本无以为继的帝国财税体制迫切需要转轨。

从海外流入的白银, 首先在南部的广东等地区用作货币,此后在1423年传到长江下游地区,并成为法定纳税货币。其他省的税收自1465年起也以白银的形式上交国库。于是,自宣宗朝开始的折银税改直到嘉靖朝时,在桂萼的大力推行下才纳入正轨,试点推行。神宗时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矛盾也随之尖锐。于是张居正强力确立“一条鞭法“,从此“役归于地”,自唐朝两税法至今,中国财税体制终于基本完成转型,从反复错杂的人丁税和雇役体系中脱身,抑制了官僚盈利经纪体系而增加了税收。
此法一经推行,成效显著,“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并且“计亩征收“,“役归于地”,使得劳动者的负担得以减轻。但是,此时的帝国随即便陷入了“黄宗羲陷阱”:各种名目的税赋经并税改革得以整编简化,但名目繁多的税种又很快重现,以致赋税持续攀升,甚至比改革前的税制更为腐朽混乱。
而“三饷”的摊派,便是这一陷阱黑洞的反噬开始。根源似乎是帝王的吝啬,从来“以天下奉一人”,完全不顾及百姓之社稷与祖宗之江山。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仅仅附着在明帝国,似乎各个大一统帝国都因无法有效处理好央地关系、协调君臣关系而陷入这一帝国维持统治的死循环。
但静下心来分析,三饷摊派之下不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可说是微乎其微。即使面对关外辽东和陕北流民的威胁,也只是先后“援征倭、播例,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岁额……”而诸如黄宗羲等人认为的急剧爆发的财税抬升,其实是很值得商榷的。但“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周期性财税制度波动却显而易见。当清朝中晚期内外交困时,也无可避免地滑入“黄宗羲陷阱”,厘金的摊派也丝毫不比“三饷”逊色。
统而言之,这是大一统中华帝国躲不掉的陷阱,以集权政治统摄下的封闭体制,自上而下掌控经济,最后往往会掉入各方势力的利益角逐,“原则上不让步,实施上不坚持”的帝国制度逻辑漏洞也就形成了“正式与非正式”体制间的微妙关系,而坚持君主专权的集权帝国注定无法跳脱,只能循环周期式的跌入“黄宗羲陷阱”。
参考资料:《明史·食货志》《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十六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