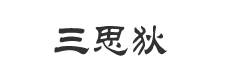是的。情况如下:桑坡村属于河南省孟州市。孟州桑坡村被称作“中国皮毛之都”,全球最大的雪地靴品牌UGG的代工厂——“隆丰厂”就在这里的小镇上,每年为UGG代工生产大量产品,还向周边数百家没有品牌的雪地靴生产企业供应羊皮毛原材料等。
一、孟州市南庄镇桑坡村西距孟州市区7公里,是孟州市最大的回族聚集地。

桑坡村应为孟州市最古老村名之一,村名桑家坡确因姓氏而来。明《怀庆府志》记载,村名来自五代时期后晋(936年—947年)宰相桑维汉葬在村北清风岭阳坡上,因北高南低,自然成坡,故取村名桑家坡,简称桑坡,所以说桑坡之名由来以久。明正德《怀庆府志·孟县村庄》称立义乡桑家坡村;清称立义乡立信里桑家坡;民国改属二区,分称东、西桑坡镇;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属二区;建国初期,属二区,1953年改为桑坡乡;1958年属南庄公社,建立桑坡大队;1983年社改乡,后乡改镇,称桑坡村委会。
桑坡村坐落在清风岭下,桑坡是清风岭的一段。
清风岭,也有写作青峰岭的,其实就是一道不高的土丘岭,原经市区十字、马桥、庙底、南庄村中心街而过的新孟路就是建在清风岭脊之上。
清风岭可能是黄河冲积平原的顶部,蜿蜒曲折,宽约3-4公里,发端于孟州市的大、小宋庄,在老城区北门外称笔架山,经梧桐村过上段渠村,绕过缑村,经梁村称梁村冈,其上有司马家族墓地,四司马墓志就出土于此,还有清礼部侍郎薛所蕴墓,经桑坡村,称桑家坡,经沇河村,有司马懿的兄弟司马馗家族墓地,经温县,在武陟境内没于黄河,长约50公里。几十年间,地貌变化,清风岭已几乎变为平地,更别说悠悠岁月,沧海桑田,变化万千。
桑坡村应为唐时已有的村名,回族的族源虽也可以追溯到唐代,但学术界一般认为回族大致形成于明代,这就是说桑坡村明代之后才有可能成为的回族民众的聚集地,那么桑坡的回民的来源是什么,是什么时候开始在此居住的呢?
二、
1991年出版的《孟县志》记载:“(孟县)回族大多聚居于南庄乡的桑坡村,系明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迁徙定居的后代。另在城内西街也有少量回民居住。”现桑坡村的三大姓丁、白、张氏的家谱也有同样的记载。如《礼拜堂丁氏谱所》内《丁君文生创建丁氏祠堂礼拜堂功德碑序》记载:“丁氏世奉伊斯兰教。自始祖讳贵由山西平阳洪洞迁河北孟县桑坡。”

明正统六年(1441),桑坡村的马姓人家逃荒到沈丘县槐店,《马氏宗谱》记载:他们原是西北枣林庄回民,明洪武、永乐年间不断地被官府集中到洪洞县南门外广济寺内树身数围、荫蔽数亩的大槐树下,发“凭照川资”,被迁往豫北怀庆府孟州诸地,因其源自“大槐树下移民”,又围清真寺而居,故把此地称做“槐坊”。槐坊《马氏宗谱》还对迁徙地进行进一步说明:“吾宗马氏世居山西洪洞县,三迁以至项城之南顿”、“初居南顿石桥口,河北怀庆府孟县桑家坡人”。说明,桑坡马氏也来自山西洪洞。
长久以来,孟州的许多姓氏,不仅回民,大多汉民的后代都说山西洪洞县是自己的老家。我曾查阅过孟州许多姓氏的家谱,除了西武章村小韩庄的《韩文公家谱》记载小韩庄韩姓为孟州原居民外,其它姓氏家谱记载几乎都是他们的祖先是明初从洪洞县大槐树老鸹窝下迁来孟州,或先是迁居别处,后又迁入孟州。其代表特征都是:他们把上厕所说是“解手”,他们的脚小指都分两瓣。
根据《明史》、《明实录》记载:自洪武六年(1373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近50年内,先后从山西移民移民达18次,其中洪武年间10次,永乐年间8次,约90万人。移民主要出自山西的泽州、潞州、沁州、汾州和平阳府,主要迁往山东、河北、河南等多个省的约220多个县。从这个史料来看,移民区域之中并没有洪洞县,仅有洪洞县的上级平阳府。即使是山西洪洞《大槐树志》也是同样记载:“大槐树在广济寺之左侧,明代洪洞洪武至永乐年间,曾七次在此地集中泽、潞、沁、汾和平阳‘有丁无田’、‘丁多田少’之户徙居彰德、卫辉、怀庆、大明、广平、张家口以及凤阳一带部分地区。”也没有提到称民出自洪洞县大槐树下。
中原各地居民来自“洪洞移民”的说法,自明至清一直在留传,但在官修的正史《明史》、《明实录》和其它正史中都没有提到。记载“洪洞移民”这件事的主要来自地方志和各地家谱,尤以家谱为主。第一个记载“洪洞移民”到中原各地的地方志是民国六年(1917年)编撰的《洪洞县志》。
史书、方志、家谱是中国史料体系三大体系,但三者中可信度、权威性,以史书为最,方志为次,家谱最低。方志、家谱多为地方和家族所修,经常存在一些考证不严、牵强附会、引用不确、前后不一等问题,一般在历史考证上,方志和家谱所记载的内容不作为考证依据,仅作为参考资料,所以说史料价值有限。

针对大槐树的传说,学者赵世瑜在《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个看似虚构的传说使我隐约感觉到族群关系与大槐树传说的关系……到明朝开始重塑汉族正统时,人们要想办法证明自己的族源,实际上已经不能说得很清楚了,因此到这个时候人们就需要塑造一个祖先的来历……洪洞移民传说,与客家宁化石壁传说、广东南雄珠玑巷传说等一起,可以看作是祖先同乡传说的类型。这种同时期迁居的传说并不问迁居者是否同乡,而是迁移时集中于某地域的时间相同而己。很显然,这是他们利用各种资源重构自身历史的作法,是自我建构历史的典型。”
也就是说,桑坡村回民来自山西洪洞的记载是有待商榷的。如果桑坡村的回民不是从山西洪洞县迁徙而来,那他们就应当是孟州原有居民,明代之前已在孟州居住生活。那么,桑坡村的回民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三、
明代之前,回回还不能称为一个民族,因此不能等同于回族。“回回”一词,最早见于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是指唐代以来安西(今新疆南部及葱岭以西部分地区)一带的“回纥”人(“回鹘”人)。“回回”可能是“回纥”、“回鹘”的音转或俗写。南宋时,“回回”除包括唐代的“回纥”、“回鹘”外,还包括葱岭以西的一些民族。这都和现在所说的“回回民族”不同。十三世纪初叶,蒙古军队西征期间,一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以及波斯人、阿拉伯人,不断地被签发或自动迁徙到中国来,许多人加入了蒙古大军,随军远征。1234年蒙古国联合南宋灭掉了金,孟州就纳入蒙古国的领地之内;1278年忽必烈率领元朝大军灭掉南宋,统一全国。这样,回回人作为元朝的二等公民的色目人,以驻军屯牧的形式,以工匠、商人、学者、官吏、掌教等不同身份,散布在全国各地,这些人一般被称为“回回人”,时间长了他们就自称自己是“回回”人。
据乾隆《孟县志》:元时孟州称怀庆路孟州府,管辖河阳县、济源县、温县。有元一代,怀孟路、孟州府和河阳县的多任官吏都由回回人担任,他们是:曷思麦里:西域人,太祖时领怀孟奥鲁,太宗时怀孟达鲁花赤,又怀孟河南甘八处都达鲁花赤、捏只必,曷思麦里子,太宗时怀孟达鲁花赤、纯只海,散术台氏,太宗时以京兆行省都达鲁花赤镇怀孟、密里吉,曷思麦里次子,宪宗时怀孟达鲁花赤、阿里,中统间宣差孟州达鲁花赤、段塔剌浑,中统间孟州通事、夹谷忽鲁忽都,中统间权知州事、脱来公,蒙古人,至元五年,知河阳县、谢伯颜察儿,鄄城人,至元六年,孟州同知、完颜居仁,至元间孟州知州、钦察公,至元间孟州达鲁花赤、抄海,至元二十三年,孟州达鲁花赤、伯帖木儿,西土人,曲枢之孙,大德十一年,怀孟路总管府、脱不花,至大间孟州达鲁花赤、怯来,至大间孟州达鲁花赤、怯烈,至大间孟州同知、八都儿,至大间孟州同知、完不班,至大间河阳县达鲁花赤、也迭女儿,至大间河阳县达鲁花赤、和元谅,至大间河阳县尹、胡讷,至治元年,孟州知州兼管诸军奥鲁事、虎都都鲁弥实,至治元年,河阳县达鲁花赤、铁木儿不花,泰定二年,孟州达鲁花赤、完颜贞吉,后至元六年,孟州知州兼管诸军奥鲁、赛也列失,后至元间孟州达鲁华赤兼管诸军奥鲁、王伯颜察儿,至元元年,河阳县尹、孛兰奚,至正四年,河阳达鲁花赤、塔察儿公,至正间孟州郡监、悯安荅儿,至正十年,河阳县达鲁花赤、哈剌八都,至正十年,河阳县主簿等等。
这些人中,曷思麦里祖孙四代都曾在怀孟为官,一个家族长期在一个地方为官,就会出现了“官迹所至,因民寓家”现象,这些回回人的家族和他的部下也多为回回人,也就逐渐在怀孟一带定居下来。
明灭元之后,朱元璋虽然也颁布了“禁止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限制回族内部通婚,采取强迫同化”等政策,但朱元璋“御制至圣百字赞”以及明皇室关于修建清真寺和保护清真寺宗教职业人员的谕旨,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回回人的宗教生活。这样在伊斯兰教义的影响下,以回回人为主体,融合了国内汉、维、蒙等多种民族成分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回族。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回族人开始逐步内附,分散到全国各地定居。但因不同的民族信仰“同类则相遇亲厚,视若亲厚,视若至亲。” “自守其俗,终不肯变。”形成了以清真寺为核心的共同文化,也形成了一个个固定的回族聚集点,自成村落。
桑坡村最终也应是这样形成的,《桑坡志》也有同样的记载:“至明朝万历年间桑坡已小具规模,清朝初年桑坡已成为一个大村庄了”。桑坡村二十四姓之中哪几支是元代回回人的后代留下来的原居民,哪几支是明代之后从其它地方迁徙于此定居居下来的,还有待更详实的史料来进一步考证。
总之,桑坡村的回民主要来自元朝建立以后留居在孟州的回回人的后代和明清之际从各地迁移而来的回族。
明代之前,孟州的姓氏见诸史料的就有一百个以上,如韩、王、张、李、苏、梁、宁、桑等等,他们的后代之中肯定有世守桑梓的,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眷恋故土,即使是元未明初的惨烈战争,也不可能使这些孟州姓氏的后代全部背井离乡,远走它方。但现在保存记载来的绝大多数明清家谱却记载他们都来自山西洪洞,这里就存在着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有学者把它称之为“祖先同乡移居传说”现象。
祖先来源各不相同的姓氏却流传着“祖先同乡移居传说”这一现象,在中华文化发展和形成的过程中是一个传统,不可忽视。如中国的姓氏几乎都来源于姬姓和姜姓;再比如,中国人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这一现象有着非常积极的一面,它不仅为超越、融合不同的世系与民族提供了绝好的借口,而且也提供了一个包装隐藏其本来身份的最理想形式,这一形式最终成为了中华多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牢不可破的粘合剂。(梁永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