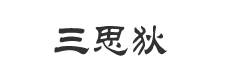《野狼Disco》之所以能火起来,不仅因为歌词旋律朗朗上口,还有它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借助回忆90年代的娱乐方式与粤语流行历史,来肯定如今的生活。
之后,野狼Disco被曝侵权后禁播。
在之前有一首歌很火,叫做《野狼disco》,有人说,这是东北土嗨,是喊麦,也有人说,你懂个屁,这叫废土音乐,这叫蒸汽朋克。
不在东北住个几年,是不懂这歌的喧嚣、骄傲、自卑和寂寞的。
东北这个地方,曾经是中国的荣耀,东北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他们再没落,人口再流失,厂矿工业再萧条,他们城市的生活水平,其实比中国大部分地区人口是要高的。
特别是东北人的平均教育水平,艺术修养,会让你大吃一惊的,你随便在老城区里找个卖菜大妈,说不定能和你唠方程、讲历史、唱歌剧。你随便找个大金链子中年人,说不定能和你谈文学,讲音乐。
不信?不信你随便找个东北城市住一段时间,找几个东北老哥老妹唠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野狼disco开头那一段儿土嗨粤语,换了在中国另外任何一个地区,都没有这种孕育这种调调的土壤。东北曾经是中国最发达、最现代化的地区之一,改革开放之后,也是港台文化传入最快传入,最快生根发芽,最快浸润传播的地方。
再加上东北八九十年代国企改制,很多人下岗,大批的青年没事可干,从热血阳刚的工人阶级,变成了游手好闲的社会人,集体主义价值观崩塌,自由散漫萌生,香港市井小资文化一传入,刚好无缝对接。

他们甚至比真正的香港人还能玩解构,玩自嘲,绣口一吐,就是“心里的花,我想要带你回家。”
东北人语言天赋出色,吹牛逼都能押韵合辙对仗工整,顶针回文赋比兴玩得行云流水,天生对音节韵律敏感,爱说爱笑爱唱爱热闹,所以,目有所见,心有所感,一嗓子吼出来,就是“左边画一条龙,右边画一条彩虹”了。

当年,东北是“共和国的长子”,因为时代和国际形势的原因,全国最优秀的人才,都赶赴白山黑水,去建设中国的重工业,去奠定共和国的根基。他们把青春和热血,都留在那块土地上,你现在去东北,之所以随便遇到一个大爷,都觉得他文化水平不低,那是因为,在当年,他本来就是国家最优秀的人才之一。当年的东北,还是中国的粮食、能源、工业产品的输出之地,支援着整个新中国的建设。
然而,时代变了,当国际形势改变,东南沿海崛起,市场经济繁荣之后,东北忽然之间,就成了上个时代的传说了。人们容易形成刻板印象,认为东北如今输出的,就是烤串儿、喊麦、快手老哥.....和“你瞅啥”?
我对东北的感觉,真的是一言难尽。
我去过东北最发达的大城市,也去过东北一望无际的大农村,我听过哈尔滨的阿姨唱歌剧,我也见过黑土地上的农民四五月份踏着残雪开拖拉机春耕。但是最有趣的,是去一个寂寂无名的小地方。
2012年的时候,我还是个工程师,不是你们知乎上敲代码拿百万年薪的那种工程师,是一个月六千扛仪器改图纸的那种工程师。被总公司发配到了一个荒凉的地方,去建设一个大型监狱。那个地方很不好去,高铁到不了,普通火车也到不了。大五月的,下着鹅毛大雪,我坐着个大巴车,走了很远很远,最后一段,居然是黄土路。
一路百里无人烟,除了几个油田上的机械,啥都看不见,然后我们到了一个小城镇。那个城镇基础设施很发达,街道很漂亮,房子也很漂亮,政府大楼干净亮堂,广场开阔恢宏,到了晚上,路灯照耀犹如白昼,可是,这个城镇,这个广场,大多时候一个人都没有。
这个城镇上,只剩下一支驻扎的军队了,居民都是公务员和监狱警察,他们大多都搬出去了,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大片大片的住宅楼荒废着。偌大的街市上,只有一个小邮局、一个小卖部、一个餐馆儿、一个小修理店是正常营业的。
邮局是最让我大开眼界的,偌大一个厅堂里,就一个人上班,包裹随意洒落在地上。有一次,我的包裹来错了地方,那位大姐让我去另外一处取,我开车找到时,大吃一惊,原来是个坍塌了半边墙的农舍,昏暗的半件屋子里,居然摆着一台时新的电脑,一台的打印机,一个小姑娘在那里办业务,办公桌是崭新的,背后的砖墙年久失修,既没粉刷,还长了青苔。这里居然还有WIFI。
在这个城镇上,我这种土木狗,甚至都不需要搭帐篷住板房,因为房子太多了。我住在一个荒废的中学校园里,所有的土地、房子、花园、礼堂、篮球场、操场、跑道,都暂时是我的。我住在一栋没有人的宿舍楼里,门窗都是苏联时代的那种风格,晚上没有电,我自己一个人用柴油发电机发电。自来水系统也废了,我在花园里打了个井眼,抽出来的水都是黄色的,要沉淀很久才能喝。
如果校园里有人,从远处望去,偌大的校园里,只有我的那扇窗子,闪着昏黄的灯光。
这个校园,据说巅峰的时候有八百多中学生,这里的老师,都是当地的公务员、狱警、军人家属。后来,他们都走了,这个学校就荒废了,留给我一个人住。
有时候恐惧起来,我默默想,也许我该有一把枪,开玩笑,我这么大一个土地主,拥有这么大一片庄园和城堡,怎么也得有一条狗一把枪吧?
白天的时候,我会四处闲逛,在操场上打篮球,去花园里看野草藤蔓,看着一尊大理石雕塑,雕塑也是苏式风格,一个青春洋溢的少女,举着一个原子模型,站在齐腰的荒草荆棘中。
我还一脚踹开礼堂的大门,看见地上还铺着红地毯,每把椅子,都是天鹅绒面儿的,一些文件随意散落着。礼堂二楼,居然是个计算机机房,几十台电脑随意堆放着,落满了灰尘,我想当年,孩子们进来的时候,一定是穿鞋套的。
可惜,我当年是个钢铁直男,心里一点柔软的地方都没有,否则,我应当写出了一本出色的废土小说。
我去打前哨,主要是搞测量看图纸做预算,其他工友还都没来。我经常一个人看着蓝天白云发呆,偶尔去监狱里见甲方,能够聊天的,只有寥寥几个狱警和军人。
我比较能喝酒,在他们看来,能喝酒就算是好朋友。
他们一个个话都很多,感觉三百年没和人聊天一样,特别是喝了酒之后,有一个满脸通红的大叔,喝酒时经常唱粤语歌,很多都是我没有听过的,我唯一听懂了的一次,是他唱梅艳芳的《夕阳之歌》。
他唱完后,感慨道:“我老了,一辈子就窝在这个地方,不出去了,羡慕你们南方人,你们去的地方多,见的世面广。”
有个老爷爷,经常批评他,说小布尔乔亚就是矫情,结果他来了一段:“一个是阆宛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