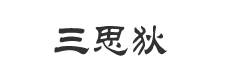“当说不当说”主要探讨伦理学上的两个问题:“应当说什么”及“说与行的问题”。
莎士比亚曾借哈姆雷特之口言“生或者死,这是一个问题”。余以为,“说”或者“不说”同样是一个大问题。
作为善于用语言表达的动物——人,一辈子要说很多话,然而,说了很多,却未必对“说”有所思。譬如:何者该说,何者不该说?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可说的,如何说好?此类问题,都值得思考。

当说与不当说
“当说不当说”主要探讨伦理学上的两个问题:“应当说什么”及“说与行的问题”。
人应当说真话,不应说谎。说真话,即按照事物的客观状况描述之、传达之,这是人类共同遵循的基本行为规范:儒家讲诚,道家修真,释家戒妄,基督教、伊斯兰教要人“不撒谎”,等等。可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亦须说明,“说真话”并非一定要“将所有真话和盘托出”,姑不言特殊职业有其保密纪律,即便普通人亦有保留隐私的权利——哪怕面对知己或至亲。故而,余以为季老(羡林)“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之信条颇具智慧,它最大限度地捍卫了人的底线和尊严。
讲到“说谎”,亦不妨略谈之。以类别言,“说谎”可大略分为“刻意”“无意”与“被迫”三种。刻意说谎,乃为达到某种目的去制造、传播谎言,此为源头之毒,当力绝之。“无意说谎”稍复杂些,它既包括未加甄别地信息传播,亦包括失真的“变形传播”。前者容易理解,但关于“变形传播”是否属于“无意”,颇难甄别。两千年前的庄子曾借孔子之口,道出其中困惑:“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庄子·人间世》)可见,使者能否把信息传递到位(其中尚涉及使者的安危),显得尤为重要。倘若使者并无任何企图而使信息有所“遗忘”,此种“失真”当属无意;倘若使者别有用心,整体上看似并未“说谎”,却刻意放大“焦点”,在情绪上添油吹火,激化矛盾,当属“刻意说谎”;倘若使者保持中正之道,践行《法言》所言的“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那么,此传言虽貌似失“真”,然因其保持中正和谐之道而过滤掉“过激的情绪”——则非但属于“非刻意说谎”,甚至属于“不说谎”。因为其选择了有限度地说真话(所谓“真话不全说”),此实则为有智慧的“信使”。关于“被迫说谎”,亦有两种,一种因不能抵制好处诱惑而说谎,一种为迫于各种威胁而说谎。两相比较,后一种在情理上尚可得到同情(但毕竟违背了道德律);前一种则应视其后果严重程度而予以道义上的谴责乃至法律之严惩。
关于说与行的问题,主要探讨诺言与善行的问题。承诺当然是“说”,但此“说”须兑现,因为不能兑现的承诺几近于谎言,不为人信任,所谓“轻诺必寡信”。鉴于此,夫子言“敏于行而讷于言”,又言“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故而,“承诺”须慎思其有无行动的意志与能力,不可逞一时的口舌之快。
至若善行,万不可心存“让天下尽知”之念而大说特说;若此,则乏善可陈。反之,做的(指善举)愈多,所说愈少,其品质愈高;至于行善而“不说”,当为上善。
能说与不能说
“当说不当说”属伦理问题,“能说不能说”则属语言哲学范畴,主要探讨语言之能指可否到达所指。语言哲学并非现代所有,战国时庄子已经提出“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之区分,几乎囊括了语言学的主要问题。
对经验领域(包括约定成俗的生活领域、知识领域尤以实证为特质的自然科学领域)而言,由于语言符号与其指涉大抵存在近乎“一一映射”的关系,故而可说。譬如,提及面包、汽车、互联网,人们一般不会产生歧义,概其属“物之粗者”,是能说清楚的。对于能说清楚的,则可大说特说。经验实证领域(实然)之所以可说,在于它能在语言自身之内得到逻辑自洽,无矛盾,无歧义。
在体验领域,譬如技艺体验、美学体验乃至神秘的宗教体验,虽可“说”,但说之效用在于通过暗示达“意”;此言“说”永远不能代替体验本身,故须“慎言”。如庄子笔下的能工巧匠轮扁,对其微妙的体验感慨道,“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同样,对于审美亦然。至于宗教的神秘体验,就更是如此了。佛教的高峰体验——正觉境界——更非语言所能描述,禅宗甚至有“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之精论,极言语言之局限。世传佛祖圆寂前曾遗“吾说法四十九年,实则一字未说”之训,颇耐人寻味:它既蕴含“人不可拘泥于语言”(不要执着)之义,亦暗含语言尚不能达到体验之本身。当然,我们亦不可因此完全否定“说”的启发、暗示作用,否则佛陀就不会“说”四十九年了。
故而,对体验之“说”(属“物之精也”)的态度,当效法《坛经》“筏喻”之说,体验虽不可传递,但可通过语言来意会,得其“意”,当登岸弃筏(指语言)。庄子所言“得鱼忘笙”“得兔忘蹄”,王弼所言“得意忘象”“得意忘言”亦如此,西哲维特根斯坦所言“登上房顶,抛弃梯子”之言,亦大致如此。
在“形上”之超越领域(属“意之不能致也”),须寡言或不说。概此形上之“物”不能显“相”于时空;或曰,此形上之物超越了语言的界限——比方说,语言的射程只有一百米,而所言(指超越之物)处于一百五十米之外,则语言无法触及之。故而,不能说。维特根斯坦甚至认为,所谓的形上体系(指哲学)根本上是语言的误用,只要进行语言“净化”,方可治疗哲学之难题。此言虽过于极端,但颇能警醒哲学家:应对日常语言与哲学语言进行必要的区分,应反思言说之分际。对于“不可说”之物,维氏给出“可说的说清楚,不可说的保持沉默”之著名论断,颇具影响力。冯友兰先生所谓的“哲学家要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熊伟先生的“说,可说;不可说,不说”之雄文皆受其影响。
其实,关于形上领域之言说,东方古哲亦早有妙论,庄子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可谓精辟;对于“不可说而非要说”的超越之道,老子亦有其“言说姿态”——勉强之说,“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尚需指出,东方古哲的超越之境虽不能“说”,但尚可体验之,故现代新儒家有“内在超越”之论,此与西方“绝缘”之超越有所区别。
会说与不会说
会说与不会说,则从“说”之效果审视之。同样的道理,同样的话,不同人“说”,效果可能大相径庭。
会说的人,若佛讲经,口吐莲花,滔滔不绝,而听者痴迷;不善说者,一言一语,亦显多余,令人生厌。
在可说、能说的层面,如何说好呢?答曰:除具备一定的学识、好的表达能力外,尚要做到识境、当机、生趣、引思——此尤针对以“说”为业的育人者,更是如此。
识境。此处之境,取宽泛义,既要明晓说者与听者所处之境,亦要知晓听者之具体境域:对象不同,经历不同、学力不同,故“说”亦当不同。孔子答“仁”,弟子出身不同,回答各异;佛陀讲经,众生根器参差,其说则有大、小、圆、通之别。
当机。“说”要当“机”,火候不到,说而无用,火候具备,“说”有大用。黄山谷学道,晦堂禅师让其参“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的话头。山谷以为自己乃儒士,竟参如此简单的话头,心中多有不快。一次山谷同晦堂禅师散步,时值中秋,一阵桂花香飘过,山谷不禁脱口而出,“好一阵的木樨”。晦堂禅师抓住此千钧一发之际,点化道:“吾无隐乎尔。”黄山谷言下大悟。晦堂禅师可谓“当机”之典范。孔子育人,“不愤不启”,更是“当机教育”之宗师,弟子三千,大成就者七十二,于此“当机”相关。
生趣。在以传播知识或教化为主的言说中,“说的对”固然重要,但枯燥的理论易让人昏沉,故“说”要讲究趣味,要因其听者兴味,故当采取灵活多样的“说”法。释迦弘法,将种种譬喻、种种偈语、种种故事融于佛理之中,故能引发听众兴趣,被喻为“口吐莲花”;《庄子》尤善用寓言讲理,雄文三十三篇,寓言故事竟多达一百五十个,难怪受到历代学人追捧。
引思。成功之“说”,须能引人入思,如此“说”之功效方大矣。孔子育人,“引而不发”,即是“引思”;苏格拉底的“助产术”,通过层层追问、层层否定,将“说”推向深入直至引发出崭新的思想,堪称引思之典范。
除此之外,尚有一种妙说——不说之说。不说,有时也是一种说,甚至是最好的说。古哲对此多有论述:老子言“知(智)者不言,言者不知(智)”;孔子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庄子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维摩诘经》言“一默如雷”;白居易言“此时无声胜有声”……种种不说,既有哲学上的“不能说”或体验上的“难说”,亦含智慧贯通或情感默契之义,此情此景,语言成了一种多余。
不说,有时也是一种境界,甚至是极高的境界。(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郭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