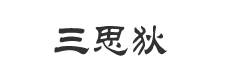关东糖的来历是,据说灶爷被玉帝派到人间来监督善恶的神仙,就在它上天的时候,人们都会给它提供关东糖,希望它吃过甜食之后,可以在玉帝面前多说上几句好话。也有人说祭灶使用关东糖,并不是用来粘住灶爷的嘴,就是用来粘住喜欢说闲话灶君奶奶的嘴巴。
每到年景渐近。孩子们喜爱的关东糖便随处可见。其实,这款糖的成品过程,与人生的坎坷经历何其相似!

京城胡同,在儿时记忆中,像一泓流淌不息的泉。其中,最为甜美的节点,是年景中的吃食。作为四合院平民之家的孩子,能一饱口福的时段,自然是进入“小年”之后、直至元宵节的日日夜夜。
记得儿时,每逢农历腊月二十三,刚迈出梦境的我,感觉晨光透入窗帘,胡同里吆喝“麻糖好香甜”的声音。悠长、甜腻感萦绕耳膜。瞬间,四合院里的孩子,攥着在家长面前软磨硬泡得来的几分钱冲出门楼,围拢在麻糖挑子周边。先要求送一点糖渣尝尝,而后,便选择“条儿顺”的麻糖大快朵颐。这类麻糖的称谓,在各地有别。京城胡同的孩子称之为关东糖。为何称为“关东”?关东在何处?我曾不止一次地自问。及至成年,我为此查阅资料,方知晓关东糖的由来。
这类“年景糖”长约4寸、成人手指粗细、外层恍若蒙一层秋霜,入口后,先脆后软、粘牙拉丝,继而就是悠长的甜蜜感。随着新春佳节的脚步声渐行渐近,齿颊间飘溢出的那份甜糯,与人们脸上的笑靥形成标配。

岂能忘,留恋这种麻糖的感觉,从农历正月一直会延续很久。直到寒假过后,直到走入小学课堂,看老师手中那细细长长、外层粘带一层粉笔末,呈乳白色的教鞭时,依然会忆起那“粘人”的糖食。我曾联想:如果用这种麻糖制作成教鞭。有谁把题答对了,可以吃上一小段,多好!
京城胡同的孩子,把这类充盈着年味儿的麻糖称之为关东糖。步入中年,我成为中国旅游权威媒体的记者。为了写民俗美食的传承,我走入国图,在权威性《食典》里,与关东糖的“根脉”不期而遇,早已远去的一幅幅图景也被拉近……
关东糖,自清代从山海关之外(俗称关东)传入京城,成为佳节甜品。在“灶王爷上天”之日(小年),出现在街头巷尾,出现在民俗专著《燕京岁时记》中。在东北三省关东糖的发源地,沿街叫卖的糖贩,一面把又酥又香、三寸长、一寸宽、扁平、呈丝条状,新出锅、刚晾凉的关东糖放在秤盘上。继而,孩子们嘴里冒出丝丝缕缕的甜味儿。

老式传统的糖作坊,设备看似简单。主要有铁锅、大缸和案板3大件。然而,制作起来,真真要费一番周折。
首先是配料较为复杂。需精选小米、稗子米、大米、玉米、大麦芽等农作物。最不可或缺的原料,自然是大黄米。东北人,俗称为糜子。
制作者配好料,用挑来的泉水淘洗数遍,直到将米糠、杂质全部洗净为止。接下来便是熬糖。熬糖的火候是关键。火候掌控不当,拔出的糖就有“皮韧感”,入口不脆,拔不出糖丝。但见有经验的糖匠,用挑糖棍从糖锅里将糖挑起,尺把长的糖丝绵延不断,白色透明。当糖锅里不再起白气泡,证明糖里已没有水份。这时,老糖匠喊声“撤火”,手下的活计马上“起锅”。接着,便开始“揉糖”。
揉糖,不仅是个力气活,还要讲究技巧。首先掌握好糖膏的温度。糖锅太热,下不得手;糖膏太凉,就会变硬揉不动。每次只能揉5斤左右,身材魁伟、精神矍铄的汉子,抓紧时间、一气呵成把糖“揉熟”。这其间,饿了不能吃,渴了不能喝。更不可能有如厕的时间。将糖揉好之后,制作者一声洪亮之声:“开案”!所谓开案,糖业行话叫“拔楦”或“拔糖”,为最后一道工序。只见两个人对面而立,各自抻着一个糖膏头,将糖抻到一定长度,一方将糖膏头往上一合,喊声“接着”,对方应声“来了”,接着再抻拉。反复多次,糖膏越拔越白,越拔越细,最后要拔出“蜂窝”,放到案子上,加香料,压为条状,然后冷冻,关东糖由此亮相于闹市。
一款年景中的甜品,多像砥砺前行、饱尝冷暖甘苦的你我!煎熬过后,直到成品、直到闲静、直到面市,直到被选择者看好,直到与味蕾互动引来微笑,成为新春佳节的美谈之一……其价值,才算完美显现。归纳起来,谁能说这过程,不是饱含叹息、历经磨难?
儿时,牙好胃健,面对这类美味,因囊中羞涩,浅尝而已,大多是饱眼福。人过中年,咀嚼、消化功能大不如前,尽管囊有余钱,可大把购买关东糖,也屡屡望而却步、在追忆中细细品味。人生世间,全方位顺心如意之事,或许绝大部分仅活跃于梦中!
尘世间的得与失,总会在半得半舍间徘徊!由此,让我想起杭城灵隐寺的那副对联。上联为:“人生哪能多如意”。下联是:“万事但求半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