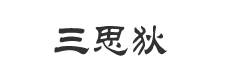经世致用提出者: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经世致用,是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经世致用一词由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提出。他们认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当时的伪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对后人影响很大。
导读: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清初三大思想家对张謇的影响
晚清时期,沉寂两百余年的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重新为经世致用的士人群体所推崇。在这样的氛围中,自青年时代起,张謇就开始接触、研读《日知录》《明夷待访录》及《王船山遗书》。在张謇的论述中,多次提及顾、黄、王三人,时间跨度近五十年之久。可以说,张謇正是深受顾、黄、王气节和思想的影响,在士人担当上追求救亡图存,在思想学问上追求实用,二者叠加作用,决定了他对“实学”与“实业”的追求。
实学与实业
顾、黄、王三人在学术上都主张回归儒家经典,以弘扬儒家学术为己任。顾炎武开朴学新风,是清学开山之祖。张謇说“亭林绝学今先河”,称赞顾炎武在学术上的开创之举。顾炎武明确提出“理学,经学也”,认为经学才是儒学正宗,主张“治经复汉”,号召人们“鄙俗学而求六经”,即摒弃理学家的语录,回到儒家经典。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至今仍是研究宋明理学最重要的著述之一。他提出“一本而万殊”的编纂原则,所谓“一本”,即“一本之先师,非敢有所增损其间”,即孔子和孔子思想。王夫之提出,“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张謇有言:“船山不死社犹存”,即王船山在学术上的构建是不朽的,华夏文化因其守护而不绝。张謇虽然鼓吹积极学习西方,但是始终坚持“中学为立身始基”,认为没有“中学”,国将不国。
明清之际的剧变促使士人群体对政治、思想与学术上的种种弊端进行深切反思,而王学末流空谈心性之弊首当其冲,顾、黄、王在批判宋明道学空疏之弊的同时,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顾炎武认为,宋明学问的根本弊端是“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而明朝亡于空谈误国。“知之尽,则实践之。”王夫之鲜明地主张行重于知,“行可兼知,而知不可以兼行”,创造性地提出“实践”的概念和范畴。张謇曾说:“我在家塾读书的时候,亦很敬佩宋儒程朱阐发的‘民吾同胞,物吾同与’的精义,但后来研究程朱的历史,他们原来都是说而不做,因此我亦想力矫其弊,做一点成绩,替书生争气。”对于儒家思想的阐发和解释,张謇更注重“经世致用”之“用”,知行合一之“行”,看重儒家思想在日用平常、现实社会的实践和事功。
“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张謇在学问上师法顾炎武,走朴学的路子,志于实学。朴学研究像“采铜于山”,重学术规范,与西方的学术方法较为接近。张謇所作《周易音训句读》一书力求通过音韵训诂方法达到对易经本义的准确理解,其中引顾炎武音韵训诂成果较多。张謇认为,朴学是讲真理实用,确能恢复儒理的本真,扫除道学的虚顽;凡是读书人,都应该往求实用的路上走。但张謇最终从治“实用的学问”转向从事“实用的事业”。张謇认为“朴学的理论,固然超过道学万万,但是讲求朴学身体力行的结果,也只能做到一个人的坚苦风格和实用的学问,于是仍无关,与人更无关,依旧是实用的空言”。朴学虽然是实用的学问,但是与社会和民生无关,因此仍是实用的空言,张謇最终投笔从商,追求“实用的实用”。
救国与实业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的话敲击人心。明亡后,顾炎武志存恢复,因敬仰文天祥的门生王炎午,改名炎武。清廷多次招致,顾炎武“耿耿此心,终始不变”“地下相逢告公姥,遗民犹有一人存”。黄宗羲之父黄尊素为东林名士,因弹劾宦官被迫害致死。黄宗羲青年时代继承父辈遗志,联络东林子弟,组成“复社”,坚持与宦官的斗争。清兵入关后,黄宗羲毁家纾难,联合抗清志士,组成“世忠营”,进行武装抵抗。明亡后,隐居著述,屡拒清廷征召。张謇在著述中多次引用顾炎武的兴亡论,诗文中不时追慕亭林,认可其“一日不死,不得不引以为耻”的爱国精神。面对列强的侵辱,张謇一直主战,反对议和。“比常读《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矢愿益坚,植气弥峻。”顾黄二人的士人志气一直激励着张謇,使得他弃官从商,立志为百姓服务,于社会有益。
“国之存亡,已不忍言,不亡亦必与之争,既亡尤必与之争。”张謇认为,其时之中国“国不亡而日演亡国之事”,即清王朝虽然没有灭亡,但是每天都有可能灭亡,因此再讨论国家的存亡已无意义,可见他的万般无奈。因此,中国最紧要的是保持文化和精神,认识到自强之道——实业救国。整个民族如果都不能适应工业化,那只能被工业文明所淘汰、灭绝;但是,如果整个民族能够积极学习工业化,精神上又有儒家思想支撑和维系,即使国家被灭亡也能恢复国家。
《马关条约》签署之后,外国大量的洋纱、洋布倾入中国市场,中国的棉纱、棉花、棉布进口呈几何级数增长,清王朝的主权虽然勉强维持,但市场和“利权”已全面沦陷。张謇认为,中国真正自强的基础就是实业和教育;而教育需要大量财政和社会资金投入,也需要强大的实业基础作为前提和支撑。因此,当务之急的救亡之道就是发展工商业,振兴实业。
“识得禹功兼贾策,船山不是一经儒。”张謇在读完《王船山遗书》之后有此感慨:王夫之不仅是大儒、大经学家,而且对治水和商业如此有研究。王夫之提出“大贾富民,国之司命”,即大商人和富裕的百姓是国家的命脉,认为闭关是“自困之术”,反对利用关卡盘剥商人。“民享其利,将自为之。”顾炎武清醒地看到,个体追求私利的欲望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因此要发展经济,人民“自为”即可,无须官员督导,“善为国者,藏富于民”。王夫之也提出“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的观点,肯定个体追求私利的动机和自谋其生的能力。此外,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与张謇融农、工、商为实业的思想甚为契合。
民生与实业
天地以生为德。王夫之重视易经中“生”的哲学和思想,说:“天地之间,流行不息,皆其生焉者也”,“天地之大德者生也,珍其德之生者人也”。人继承天地精神治理万物、利用万物,必尽性而利天下之生。张謇以“大生”为工厂命名,“大生”一词,正源自《周易》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即天地之大德,在于使万物生生不息。张謇的公司名称中常见“生”字,比如“广生油厂”“资生冶厂”“颐生酒厂”。张謇曾对刘厚生说:“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在张謇看来,儒者的本分是让百姓有饱暖,即孟子所谓“黎民不饥不寒”。
王夫之认为,真正的圣贤应该“不专于己之天”,而应贴近人民,体察民心,扶助百姓,反对“舍民而言天”。“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黄宗羲也强调为民出仕做官。这些思想对于张謇看透官场和仕途,决意实业救国有促进作用。张謇提出“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张謇立志为百姓尽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不是服侍所谓贵人,当不能为百姓有所作为的可耻之官。
顾、黄、王三人精神、气节、学问、担当一直激励着张謇,凡事只要有利于鼓新气、祓旧俗、保种类、明圣言,张謇都不畏艰难,勇于担当,全力以赴。“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明清之际经世致用思潮发展的极致之一就是士人从事实业,通过做事改变自己、改造社会,张謇是其中集大成者,开风气之先。
1904年,张謇给学生出过这样的作文题:《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志业与田子泰孰近论》,将黄、顾、王三人与田子泰相比。所谓志业,即志向和事业,“近”即切近时弊。田子泰即田畴(169年—214年)。在东汉末年的乱世当中,田子泰率领宗族及一同依附的几百人进入徐无山中,耕种兴学,教书育人,百姓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周边百姓纷纷聚拢,几年间聚集了五千多户人家,乌桓和鲜卑也派遣使者送贡求和,不再侵扰边境。田子泰是儒家士人,他的乱世自治成效卓著,因为人民自强不息,连夷狄都不再侵扰;张謇相信实业可以救国,国家如果自强,外敌也不再侵犯。
张謇出作文题时,心中显然已有答案,即在顾、黄、王不断反清复明,志不得而隐居著述之外,还有“田子泰式”的经世致用路径,即带领一方百姓,实业自强,垦荒兴学。其时,张謇的纱厂事业蒸蒸日上,张謇地方的威望、社会的名望也迅速抬升,张謇兴奋于找到新的圣贤模范。他将创办的垦牧公司厅堂题为“慕畴堂”,追慕田子泰为榜样。此后的二十多年间,他父教育、母实业,力求把家乡南通建成全国模范县,像田子泰一样聚拢百姓、扶助民生,更为重要的是,他志在做“开路先锋”,希望更多有识之士效仿,致力于实业和地方民生,为社会做出一些实用的成绩。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梁林军(南通大学张謇研究院特约研究员)